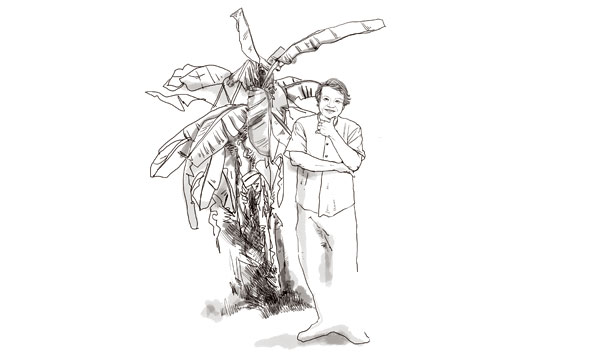
錢津寧 插畫
陳瑞獻
1943年生於印尼蘇門答臘哈浪島,原籍福建南安,現為新加坡公民,新加坡首席多元藝術家。創作小説、散文、詩歌、戲劇、評論,寓言、油畫、水墨、膠彩、版畫、雕塑、紙刻、篆刻、書法、攝影、服裝設計、行為藝術、大地藝術。1987年與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一起入選法蘭西藝術研究院駐外院士,2005年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設立“陳瑞獻藏室”,2006年新加坡郵政發行11枚“陳瑞獻藝術系列”郵票。陳瑞獻擁有三家個人藝術館:新加坡的陳瑞獻藝術館、正雲樓以及中國青島小珠山的陳瑞獻大地藝術館。
本報記者 李懷宇 發自廣州
陳瑞獻是一個獨特的藝術家。他嘗試過小説、散文、詩歌、寓言、戲劇、評論、翻譯、油畫、水墨、膠彩、版畫、雕塑、紙刻、篆刻、書法、攝影、舞美、服裝設計、行為藝術、大地藝術。1979年獲法國國家文學暨藝術騎士級勳章,1985年獲法國藝術家沙龍金獎章,1987年獲選為法蘭西藝術研究院駐外院士,2003年獲新加坡總統卓越功績服務勳章,世界經濟論壇水晶獎,是新加坡獲獎最多暨亞洲區潤格最高的藝術家之一。2012年12月2日,在北京保利舉行的“現當代中國藝術夜場”中,陳瑞獻的作品《月圓時候》以1897.5萬成交。
“藝術是謊言”
除了創作,陳瑞獻每天都寫日記,四十年從不間斷,就像做賬一樣,密密麻麻地寫着,偶有靈感,則用短句形式記在日記邊緣。如果一年中能夠得到十來句妙語,他會説:“我去年的進賬不錯啊!”
閒談中,陳瑞獻提到南美洲畫家波特羅(Botero)的“藝術是謊言”的説法。“這個概念我也在"古樓畫室"的常年展上提出。詩人高克多説:"藝術是説出真相的謊話。"畢加索、方士庶、羅多華諾維克以及多位大師也這麼説。這是對藝術創作與藝術欣賞至關重要的概念。藝術家常從造化與現實中的事物得到靈感,以他的靈見、激情、哲思及想象,對通過感官與心識所感知的事物,加以減化、扭曲、增添、改變、重構、再造,將之變成高於自然的歌德所謂的"第二自然"。”他進一步闡述,“蘇東坡畫在紙上的朱竹,讓人誤以為它是園中那株竹的照實描繪。有人問,"難道有朱竹嗎?"蘇東坡答,"難道有墨竹嗎?"看看馬蒂斯以他的方法反映出來的真相,那便是他不畫事物而是選擇描繪它們之間的不同。畢加索的情況呢,那是他依據想象而非他所看到的對象畫畫。藝術家很清楚天空是藍色的,所以他把天畫成綠色。就像塞尚筆下的藍蘋果與畢加索筆下的扭曲的鼻子,那迷人的綠天空使觀者重新去注視天空,他長久以來因為熟悉而對它漠不關心,這一來他就重新發現天光與彩虹的鮮麗,還有他的明覺敏銳。他發現藝術自成一個世界。”
陳瑞獻對弘一法師和豐子愷的藝術頗為傾心。他説:“豐子愷是弘一法師的弟子,是一個領悟力表達力至高的作家漫畫家。他主要的特長是文學的感覺敏銳與意象豐富,一般先有一個好意念,一句好詩,一行美文,一個平凡的生活片斷之後,才用風格很簡約的構圖將它表達出來。意筆草草如日本的竹久夢二,也像一方方齊白石的印文選得好刀張又恰如其分的篆刻小閒章,寓意深長。”在陳瑞獻策劃的廣洽紀念館,館藏的豐子愷的書畫之多,可説是海內外之冠,因為豐子愷與廣洽法師情同手足。豐子愷有一張給廣洽法師拂暑的扇面,畫一對姐弟笑哈哈扛着一個跟他們的身體等大的大西瓜,上題“種瓜得瓜”,他用童心、用藏書票的小格局來弘揚高深的佛理。豐子愷的《護生畫集》一共畫了八冊,全部由廣洽法師在新加坡出版。《護生畫集》第一、第二冊是豐子愷跟弘一法師合作,弘一法師題詞,豐子愷畫畫。“《護生畫集》警世的味道更濃,但仍充滿了一種天真爛漫的色調。”
新加坡作家絕對養不活自己
陳瑞獻認為宗教與藝術的結合是世界文明的共同現象。“一般所説的佛教藝術是指通過雕塑與壁畫而完成的膜拜供奉的對象,最初的出發點不是在搞藝術,而是善男信女為了祈福求平安而做出的善舉,供奉一尊佛菩薩。宗教與藝術的靈妙結合,還顯示在藝術家對創作的觀瞻的改變:佛教的玄秘主義結合道家的自然主義與儒家的人本主義,而形成的禪宗思想,從根本處改變了一代代文學藝術的創造者,像宋代的山水畫家,明清的文人畫家以及現代東西方多個心靈流派的創作家的人生觀、宇宙觀、創作觀。”
香港文化人潘耀明曾經感慨:在香港作家是不能養活自己的。陳瑞獻則説:新加坡作家絕對不能夠養活自己。“有一個自稱能以賣文為生的作家,那是全世界都知道他在吹牛,只剩下他自己還在假裝不知道自己在吹牛的作家。”陳瑞獻説,新加坡的種族與語文生態的多元化比香港複雜得多。“我們是多種族多語文,我們的行政工作語文是英文,我們的國語是馬來語,那是出於政治平衡的一種需要。我也懂馬來語,早年考公民權,還要考馬來語文,現在唱國歌是唱馬來語,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在唱什麼,我們的鈔票除了國名用馬來文淡米爾文華文英文四種官方語文的小字印上之外,其他大字全部用英文。目前只剩下幾間特選的中學可以念高級華語。在新加坡,夢想用華文寫作來生活絕對是死路一條。以英語寫作也牽涉到作家本位的問題,我陳瑞獻英文很好,要寫莎士比亞,英國人説我們不必勞駕你,而華人要用華文更能表情達意,問題是很多華人不懂華文,用英文等於繞一個大彎,毫無辦法。”但陳瑞獻笑稱,畫畫畫出名堂,可以養活自己。“不但養活自己,而且活得很好,也養活了一條街的貓狗。”
“我選擇把藝術變成哲學體系的一個注腳”
本報記者 李懷宇 發自廣州
“法國是我創作潛能成長的搖籃”
時代周報:有沒有人跟你探討過,你的畫裏面有一股南洋風情?
陳瑞獻:這是肯定的,世間充滿我作畫的題材,自然也包括自己家裏的事物。每個地方都有特別的東西,譬如這地區的特産榴蓮。白居易寫《荔枝圖序》,我們這裡寫榴蓮最好的詩文書畫還沒有出來,所以我們得多多努力。榴蓮真是我心中最愛的一個東西,我們就出了榴蓮,它可以讓我們偉大。所以,榴蓮當然也入我的畫了。南洋的紡織與蠟染色彩的運用,像褐色、巧克力顏色的運用,這些都被編進我的色彩文法中來。
時代周報:有一些藝術家年紀越大,反而是走回童年,就是在童年受教育的影響,到了成熟期以後會反映在藝術裏面,你有沒有這種體驗?
陳瑞獻:找回童心與回歸童年是兩回事:找回童心是找回自由心,是人特別是藝術家應有的懷抱與追求,像畢加索説我12歲時就畫得跟拉斐爾一樣,但我卻用一輩子的時間去學習像兒童那樣畫畫;回歸童年卻是一味追憶兒時,像夏加爾繪畫兒時在俄國鄉下的事物,偶爾為之,趣味盎然,長此以往,特別是在晚年,那是不敢面對生命流程的懦怯。
我也憶兒時,但我更強調心靈拓展的重要,就是往宇宙的無限擴大開去,越擴越大,到生命的一段盡頭,然後繼續開拓過去,一直到解脫的盡頭。我覺得文藝以後的一個方向,不是科幻,而是讓將來有修持的人,把他們往這個無限的空間透射進去,一路看到的天外天真實的現象表達出來,像虛雲大師描述他到兜率天看到會泉長老一群老友的情況,那會是多麼新鮮的創作。問題是,一見到菩薩世界,還畫什麼畫寫什麼文章?畫畫是人間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消遣,一個小趣味,只希望這個小趣味有一天能夠舉頭望到頭頂那個天,多點新鮮感,要不然,一直要往回頭走,奢望能回到無望的童年,越搞越心慌。我是向無限的未知,慢慢向前去。
時代周報:你在南洋生活,但是中國文化對你的影響、熏陶是深遠的?
陳瑞獻:中國文化是我的根本。我是華人,我從小就受華文教育。中國的朋友説:陳瑞獻在讀漢賦與莎士比亞的時候我們正沒有書讀,那個時候“文革”是整個斷層,我們這裡沒有斷。現在的情形剛好相反,是你們接了回去,我們這裡卻斷了。特別是像我這一代,我中學的時候除了讀白話文篇章也讀古文,我至今仍用文言文寫作,這是我的根。我們這裡的政治處境與氣候是很不一樣的,我更覺得愛華文是一項責任,這樣一塊寶不能丟了。我大學專攻英國文學,能用英文寫作,我在法國大使館用英法華文工作,我從小就講馬來話,但是中文不能丟掉。中文是我的母文,我很少用外文寫作,堅持用中文寫作,這是我的選擇。中國是我的文化祖國,這跟政治上的國籍與認同沒有衝突。
時代周報:從作品上可以看出來,法國文化對你的藝術影響也很大。
陳瑞獻:我剛説過,中國文化是我的根本。我創作用的主要工具、我用的語言、我用的筆墨,都在中國文化這一個很大的寶藏裏。其次,法國是我創作潛能成長的搖籃,一棵樹的根本沒有這塊肥沃土地的培養,不可能開花結果。當年的法國大使館簡直是一棟山莊別墅學堂,環境太好了。我在那裏上班,等於是在法國留學、工作、學習、創造,我跟他們一起生活了24年。巴黎一年請我去開展覽,一年請我去出席活動,一年請我專門去吃飯,一吃兩個星期,巴黎時不時向我召手,巴黎的別號就是藝術,而藝術,用畢加索的話説,“藝術從靈魂洗去日常生活的塵埃。”法國除了給我一份安穩的職業以外,還是孕育我藝術成長的溫床。中法兩國的文化累積就是我綜合吸收的養料。除此以外,世界各國像古波斯、古埃及、古印度文化都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尤其深愛印度文化,佛學來自印度,它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圓融透徹的哲學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