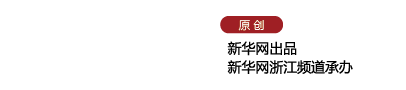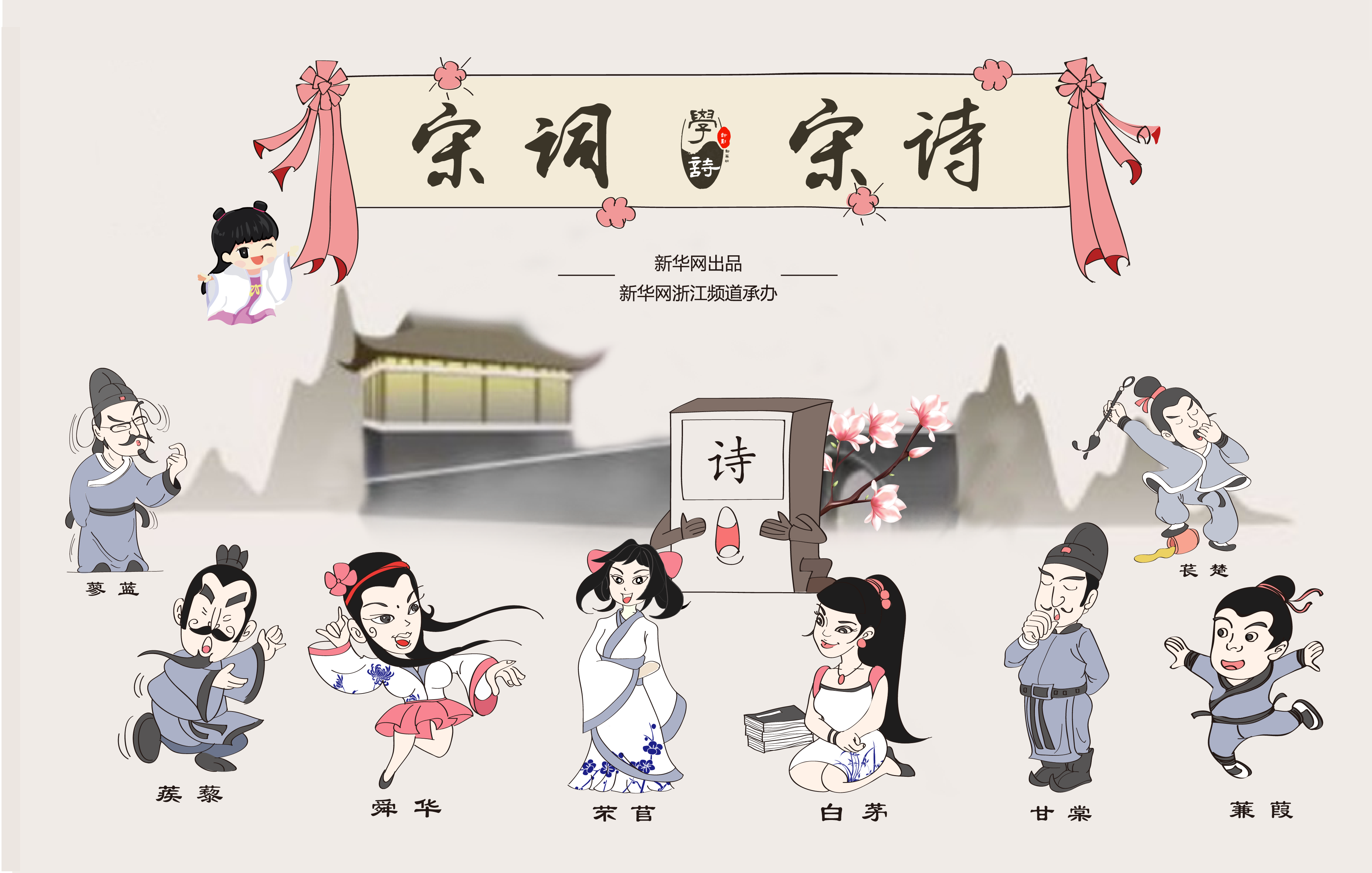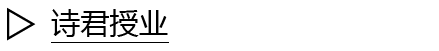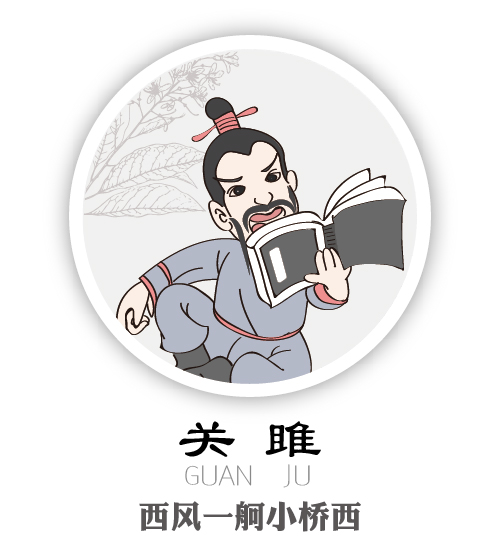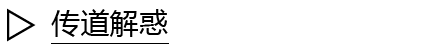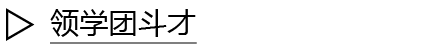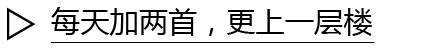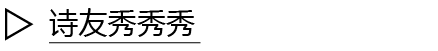這首詞是張先書寫悲歡離合的一首作品。
鶗鴂,也就是杜鵑鳥,在中國的詩詞中,這是一個悲劇的角色,所以,詞一開始作者就用兩個細節確定了作品的情感基調:幾聲杜鵑啼來、一片春花謝去,這樣的聲、色,一讀就可以感染到它的低沉、傷感,在這樣的基礎上,第三句寫的就更加令人感慨了:因為惜春,因為不希望春光逝去,悄悄地把那些已經凋殘的花朵摘了,使剩下來的顯得依然春色爛漫。這種寫法,比直説“無可奈何花落去”更能使人唏噓。
後段一節,是補足場景的描寫,雨濛濛、風蕭蕭,梅子青、柳絮白,那就是一個殘春的時節,寫的是景,烘托的是情,尤其是末句的柳樹入鏡,潛&詞非常豐富,因為“柳”是一個在古詩詞中“分離”的代號,而“無人”之柳,自然就説明伊人早已分別了。
如果前段的筆法是含蓄的,甚至沒有一個字寫人物所遇到的故事的任何一個細節,那麼後段就開始傾訴了。這裡有一個字必須理解準確,那就是“怨”,怨,在詩詞中並不就僅僅是怨恨、怨怒,古時候的字義常常會和今天有一定的距離,怨,就是離別,所謂“怨婦”,並不是有怨恨情緒的女人,而是處於別離狀態中的女人,長期未嫁未娶的人,則叫“怨曠”。同樣是宋代的詩人劉敞,在他的一首寄友詩中説:“怨極倘見思,寄聲慰離腸。”這個“怨極”同樣就是“別久”的意思。
兩人分別已久,甚至不敢去彈撥琵琶,因為怕琴弦會將離思勾起。這種離情別緒或許只能到地老天荒才會終絕,心想到此,內心豈能不百感交集,無數愁結?詞寫到這裡,六個句子都是直接抒寫內心的情緒,最後還剩兩句了,如果繼續這樣直接表白,那這個詞的質量就成問題了,所以,在詞的結尾,作者筆鋒又轉到了對景的描寫上:暮春的長夜已經快要過去了,窗外只有一鉤殘月,天猶未白。
但是,這種對景物的描寫,實質上恰恰是對人內心情感不動聲色的描寫:這種折磨人的日子,長夜無眠,直至東方之既白。所以,天猶未白,正是因為人尚未眠。
這種手段,一看就是高手了。